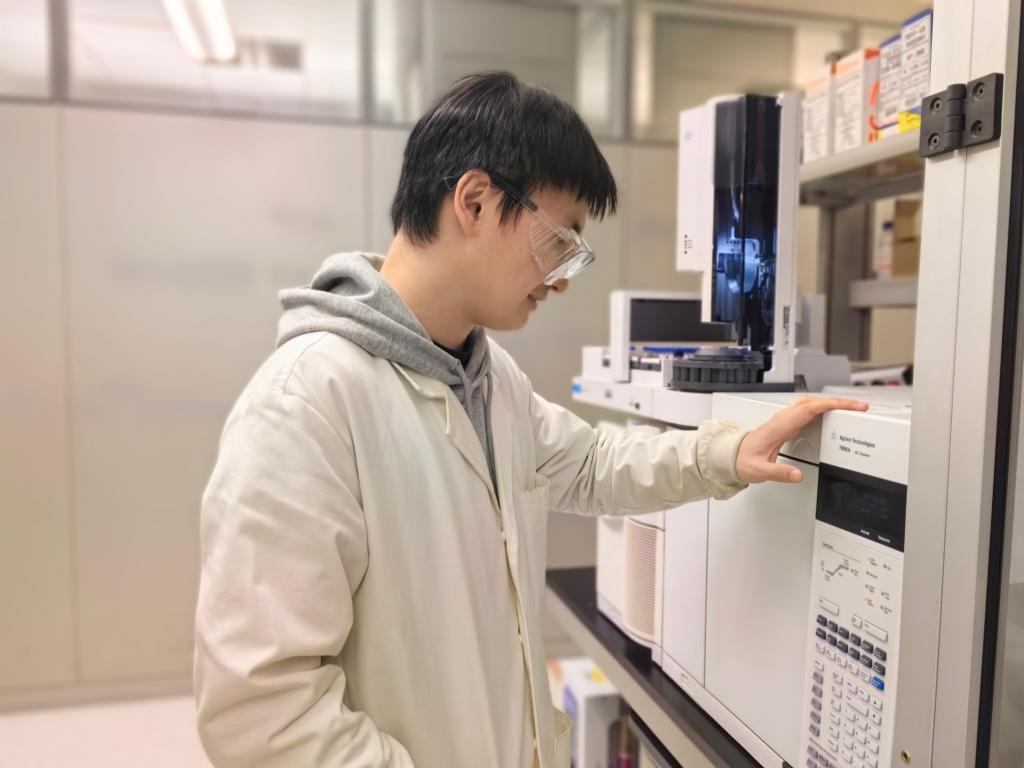劇團2022年在晉江演出。 東南網9月25日報道(福建日報記者 莊然 通訊員 王婷婷 文/圖) 法蘭克福劇場燈光漸暗,一束追光刺破黑暗。70歲的姚義炳立于臺側,指尖輕顫,懸絲下的穆桂英倏然揚眉,翎羽翻飛如電。異國孩童屏息的寂靜中,那縷絲線,正牽動著一個家族百年的漂泊與堅守。 今年5月18日至21日,作為非遺代表性項目提線木偶戲(福鼎)的省級代表性傳承人,姚義炳隨福建省政府代表團赴德參加文旅推介會。這是他自去年9月受邀參演得到德方各界高度評價后的第二次木偶文化出海之行。 從他的口中,記者感受到的是熾熱的藝術人生。 【懸絲春秋】 “一年里有330多天都在演出或訓練。”日前,姚義炳剛從浙江演出回到福鼎。他介紹說,姚氏劇團正嘗試創作新劇目,涵蓋鄉村振興、太姥山傳說、白茶文化等主題,“既要尊重傳統美學,又要創新內容形式,民營劇團只有觀眾認可,才能發展”。 不同于福建其他地區的木偶戲,姚氏劇團將傳統木偶戲表演與京劇藝術相融合,形成“通俗而不失嚴謹”的表演風格。其京劇的唱腔、臉譜和表演程式,在閩東、浙南地區獨樹一幟。 “劇團是我父親創立的。”姚義炳的思緒回到上個世紀。 1953年,福鼎城關戲臺鑼鼓喧天。姚義炳的父親姚仁貴手提新刻的木偶登臺亮相,滿座皆驚——木偶衣飾華彩奪目,唱腔竟是字正腔圓的京劇西皮二黃。 這位從閩東鄉野走出的藝人,以獨創的“京劇提線木偶”開宗立派。當時的閩浙邊界,木偶戲班林立如繁星。姚仁貴從唱腔、服飾到偶頭雕刻全面革新,一改土腔土調,“仁貴班”迅速脫穎而出。 每逢年節,兩省邊界鄉民以請到“仁貴班”為榮,班社鼎盛時演員達20余人,巡演足跡遠抵浙南。 幕布后,年僅8歲的姚義炳在煤油燈下蹙眉苦背《小開門》曲牌。姚仁貴立于身后,戒尺在掌心輕叩:“三夜背不下,莫想上戲臺!” “學藝雖苦,卻充滿趣味。多虧父親當年的嚴格!”姚義炳感慨道。然而12歲首次登臺時,他還是演砸了—— 那夜油燈熄滅后,姚義炳蜷縮在打補丁的被褥里,淚水洇濕蕎麥枕。線繩在指尖勒出的血痕火燎般灼痛,父親當眾的叱罵猶在耳畔。啜泣聲在寂靜中格外清晰,驚動了巡夜歸來的姚仁貴。 粗糲的手掀開粗麻蚊帳,油燈映亮父親的臉。看到兒子腫如核桃的眼,這位素來冷硬的班主喉頭滾動,終是坐到床沿,用生滿老繭的指腹揩去孩子面頰的淚:“疼?莫怨爹嚴苛。”他將兒子小手攏入掌心,線繩勒出的紫痕刺痛雙眼:“戲比天大!白米飯多珍貴啊,老百姓不舍得吃,給我們,對得起他們嗎?” 見兒子抽噎稍止,姚仁貴從懷中摸出塊麥芽糖塞進他嘴里,聲調陡然溫軟:“你現在吃苦頭,往后才有真甜頭。”晨光初透時,姚義炳迷迷糊糊感覺身上一暖——父親用熱毛巾替他敷著紅腫指尖,那佝僂背影在窗欞間定格成永恒剪影。 轉眼到了20世紀80年代,“姚家班”大旗仍獵獵作響。年演300余場,“閩東第一家”名號響徹閩浙邊界。提線木偶是養家“金飯碗”,姚義炳與父分授學徒,門庭若市。鼎盛時,戲箱裝滿5架牛車,夜宿祠堂常有村民端來熱騰騰的粉干蛋酒。 未料時代洪流驟至,電視熒屏很快帶走了絕大多數觀眾。最后一場封箱戲后,姚仁貴顫手撫過相伴半生的關公木偶,老淚縱橫。劇團解散夜,姚義炳獨坐空箱上,院中桂花簌簌落滿肩頭。 【拈花化偶】 “劇團解散后的那些年,我一直輾轉外地經商。”姚義炳說著,眼神一暗,指間煙蒂微微發顫。“可心底那團火——對木偶戲的癡念,從沒熄滅過。” 2010年臘月,寒霜凝窗,已下海多年的姚義炳蹲在舊戲箱前點煙。橘紅星火明滅間,箱底泛黃的宣紙赫然入目——那是20世紀50年代“仁貴班”在浙南連演33場的戲單,墨漬已被歲月洇成淡痕。 但重建戲團談何容易。“第一關就是錢。”姚義炳說,“好在老伴愿意支持我!” “蓋房那年,你天天說‘夯地基如走臺步,一步踏錯全盤歪’。這房,就是咱們的戲臺!拆了戲臺——”老伴喉頭哽咽半剎,聲調陡然升高,“就為續上那縷弦音!” “爹,您攢的招牌不能砸我手里。”姚義炳攥緊房本沖出家門。過戶簽字時,姚義炳手中的筆三次滑落,墨點濺如淚痕。賣房的錢,當天便換成燈光音響,空蕩庫房里新漆的“福鼎市姚氏京劇劇社”木牌映著光,恍若當年父親在祠堂掛起的“仁貴班”匾額。 首演當天,暴雨傾盆,山路被泥石流阻斷。60多歲的姚義炳率學徒扛箱徒步,膠鞋深陷泥濘。 行至溪澗,學徒腳底打滑,系著穆桂英木偶的戲箱眼看要落水。“護箱!”嘶吼聲中姚義炳撲身墊底,箱角重重撞上肋骨。待爬至村寨,眾人滿身泥漿,臺下僅3名拄拐大爺守候。 “開戲!”姚義炳吞下止痛片提線上臺。雨聲如鼓點,《定軍山》唱腔穿云裂石。曲終時,90歲的畬族大爺捧來姜茶:“這聲黃忠刀劈夏侯淵,我50年前聽過。” 3年間,新劇團走遍閩東182個村落,年均義演210場。常有觀眾不足10人,老姚仍唱足全場。這股不服輸的勁兒,讓星火終于燎原。 2015年深冬,姚氏劇團創排《藍姑與白茶》,學徒們以線牽花模擬采茶舞,暗香隨舞步流轉,戲中“白茶祭山神”的絕活自此誕生——木偶翻越臺階,白瓷茶盞在木偶手中紋絲不灑。劇團展示的融合太姥文化與白茶文化的傳奇故事讓觀眾嘆為觀止,得到社會各界廣泛好評,火爆出圈。 “劇團‘活’了!”姚義炳憶及往事,眼眶微紅,“從解散邊緣重回正軌,如今團隊已發展至10余人。我們堅持商演與公益并行,尤其是‘非遺進校園’從未間斷。” 【薪火三問】 劇團雖重煥生機,傳承危機卻如影隨形。姚氏木偶融京劇魂、閩東骨,一招一式皆需十年以上磨礪。若無師傅手把手教,這百年技藝恐成絕響。 2024年,霜晨月落戲箱前,姚義炳正為赴德演出整備行裝。他驀然瞥見箱底壓著的舊戒尺——就是父親當年教他提線的那柄。尺身裂紋里積著陳年松煙墨,恰似時光浸染的絲線。 “沒有學不會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師。”說起愛徒陳方滿,姚義炳目光溫和,“起初覺著這孩子天賦平平,可他那股鉆研勁兒和對木偶戲的癡心,實實在在打動了我。” 初收陳方滿為徒時,少年提線如握鋤,穆桂英的翎羽總纏成亂麻。 一個暴雨夜,戲班返程車陷泥沼。眾人推車間,突見公路盡頭亮起手電筒燈光——陳方滿懷抱木偶箱坐在自行車后座上,一片塑料布緊緊裹著箱子,在狂風中獵獵如旗。 “老師,我怕潮氣蛀了偶頭。”少年跳下車,鞋子陷進泥水渾然未覺。箱中關公面頰光潔,他自己的褲腿卻濺滿污斑。 此后,陳方滿的父母載著孩子晨昏奔襲。只要姚義炳周末有空,清晨5時就送孩子來學早課,深夜再載著熟睡的少年歸家。姚義炳常見陳母蹲在戲院墻角,就著路燈縫補扯斷的偶絲。 最冷的臘月排練廳,陳方滿線控的藍姑偶終于能穩穩地托住茶盞。少年雀躍歡呼時,姚義炳卻看到了他凍裂的指縫——那滲血傷口里,蟄伏著比天賦更珍貴的火種。 正說著少年的故事,窗外忽傳來清亮戲腔,如今已17歲的陳方滿學藝已有6年整,可獨當一面演主角,正在院中晨練,“看槍!” 姚老將尺橫置少年掌心,“執此尺者須答三問——” “一問可耐三千場冷寂?”青年線控木偶金雞獨立:“耐得!” “二問敢闖新程辟新天?”槍尖劃出銀弧:“敢闖!” “三問可能守住這門活著的祖宗?”陳方滿線牽的穆桂英倏然單膝點地,翎羽在光塵中炸出無聲卻鏗鏘的回應。 姚老眼眶驟熱。這柄尺,終究要遞到新生的掌中了。 |
湖南通報7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問題
2025-09-26
今年以來全國稅務系統已曝光300余起涉稅違法案件
2025-09-26
陜西鎮坪一煤礦發生事故致3人被困
2025-09-26
中方再次就TikTok問題表明立場
2025-09-26
新華健康丨如何科學應對秋季過敏性鼻炎
2025-09-26
貴州省黔東南州委副書記胡志峰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2025-09-26
陜西鎮坪一煤礦發生事故致3人被困
2025-09-26
“樺加沙”減弱 廣東7300余艘船舶有序出港
2025-09-26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中國在役工業機器人存量居全球首位
2025-09-26
國家電影局、科技部等聯合印發通知開展“跟著電影做科普”專項行動
2025-09-26
- 日榜
- |
- 周榜
- |
- 月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