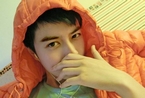聚焦扶貧搬遷困境:資金緊缺戶籍難落無地可分
www.fjsen.com?2013-06-24 11:55? ?來源:中國新聞網 我來說兩句
|
搬遷資金哪里來? 在重慶渝東北、渝西南“兩翼”地區,不少山區海拔在1500米以上,山高坡陡,自然環境惡劣,不少貧困群眾都想通過扶貧搬遷擺脫“窮根”。 本刊記者驅車4個多小時,攀上巫山縣銅鼓鎮青松村海拔近千米山坡。茫茫群山一眼望不到頭,貧瘠干旱的耕地斜斜地掛在山坡上。記者來訪時,年近八旬的村民楊振遠對于這些年最大的期盼脫口而出:“搬離這個窮地方!” 從2007年以來,青松村已有70多戶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民陸續遷走。但對貧困農民楊振遠而言,搬遷這個話題略顯沉重:楊振遠一家5口人口糧全靠5畝薄田種植玉米、油菜、土豆等;另外5.5畝退耕地每年可以獲得國家補貼近700元,這是這個貧困家庭全年能從土地上獲得的唯一的現金收入。 “我做夢都想搬出大山,但家里存款不到3萬塊錢,連在山下買個房子的錢都不夠。”楊振遠告訴記者,山上農民但凡有點辦法的,都搬走了。村里幾十畝耕地都撂了荒,成了野豬的天下,一到晚上就能聽到野豬拱食的聲音。晚上一個人坐在家門口,四周烏漆麻黑的,只有天上的星星最亮。 開展易地扶貧搬遷數年后,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戶已經搬遷,留在高山生活的農民多數比較貧困。越到后面越多的是楊振遠這種搬不動的貧困戶。 多位受訪區縣農民為本刊記者細算了一筆“搬遷賬”。搬遷成本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其一,自建磚混結構房屋成本需要800~1000元/平方米,自建或購買農房、獲得宅基地使用權的支出費用,約需12萬元; 其二,搬遷運輸費用及雜項支出,約需2萬元; 其三,部分地區要支出“入戶費”,需1000~3000元。相關法律規定,只有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才能獲得本村組的宅基地、承包地使用權。目前,跨區縣、跨鄉鎮,現在在用地制度、土地調節上沒有實現制度突破,易地搬遷過程中自發形成了一些村規民約:外來農民欲購買農房、取得承包地經營使用權,需要首先向村組繳納數額不等的“入戶費”。同時,村組還要召開村民代表會議,經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該農戶才能入戶。 而補助主要有兩部分:其一,根據新出臺的《重慶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推進高山生態扶貧搬遷工作的意見》,從今年起,重慶市高山生態扶貧搬遷對象的市級財政補貼標準統一提高到每人8000元,比去年增加了2000元。按照戶均四人計算,每戶有3.2萬元的補助資金。 其二,針對困難群眾自籌搬遷資金能力弱的現狀,重慶市明確可利用宅基地復墾的“地票”收益解決資金問題,現行價格大約是14萬元/畝,一戶半畝約7萬元。 綜合來看,在這些區縣一戶4口人的貧困家庭,易地搬遷平均花費在14萬元以上,扣除約10萬元的扶貧補助加“地票”收益,資金缺口約為4萬元。 多地干部群眾說,老百姓歡迎補助資金提高,但最根本的能讓群眾“搬得出”的政策還是宅基地復墾產生的“地票”收益。不過,多位基層群眾和干部表示,復墾和地票政策周期太長,無法滿足搬遷群眾對資金“短平快”的需求。彭水縣發改委副主任任軍說:“根據目前的地票交易政策,一塊宅基地從納入復墾規劃到地票交易完畢至少要兩年時間,而這兩年正是搬遷群眾建房急需用錢的關鍵時期。由于存在‘時間差’,群眾的籌資壓力依然很大。” 針對困難群眾自籌搬遷資金能力弱的現狀,一些區縣建議,可采取備案融資等方式,將納入高山生態扶貧搬遷范圍群眾的宅基地復墾資金提前足額支付,讓搬遷群眾有錢可搬。 戶籍產權怎么落實? 在高山生態扶貧搬遷實踐中,重慶各區縣因地制宜探索了轉戶進城搬遷、梯度插花搬遷、集中安置搬遷等模式,均涉及戶籍和土地權屬關系調整。 本刊記者在采訪調查中發現,轉戶進城的搬遷安置方式目前調整比較順利。其他搬遷模式由于缺乏制度安排,各區縣都反映存在操作困難。 按照現行法律,農村只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才能夠在本村組范圍內申請宅基地,且一戶只能有一處宅基地。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梯度插花安置和居民集中安置點接納的搬遷戶,普遍存在跨社、跨村甚至跨鄉鎮等跨集體經濟組織的情況。這些搬遷群眾的戶籍應當如何調整,房屋土地權屬證如何辦理,讓基層干部比較頭疼。 彭水縣高谷鎮鎮長羅軍告訴記者,由于戶籍和房屋產權登記等政策互為前置條件,對于跨集體經濟組織的搬遷群眾,要按照現行的法律法規辦理房屋產權就存在困難。他介紹,高谷鎮嘗試通過遷入地村組織備案的方式,假設遷入居民在當地有房子,然后辦理戶籍遷移。在取得遷入地集體經濟組織戶籍后,再辦理所購房屋的產權。 基層干部認為,高山生態扶貧搬遷很多是易地操作,市政府應出臺指導性意見,讓區縣工作有章可循,并研究放寬搬遷移民在本縣內跨村、跨鄉鎮落戶的準入條件。此外,應積極妥善解決已搬遷農戶“先上車后買票”的問題,不讓貧困群眾搬遷后喪失對房屋土地的合法權利。 此外,由于土地利用規劃問題,一些新建房屋產權也難以落實。在奉節縣興隆鎮杉木村的黃平安置點,雖然103戶居民在2010年底就住進了整齊、寬敞的兩樓一底標準“小洋樓”,但到現在,這些居民的房屋產權都還沒有拿到。 杉木村村支書陳登付告訴記者,該安置點修建時未按農用地轉用辦理手續,而是按3萬~4萬元一畝的價格從農民手中“買斷”土地來建的安置點。而即使可以通過農村建設用地“占補平衡”來調劑建設用地指標,由于土地利用規劃的限制,該安置點仍然無法辦理土地和房屋產權。 杉木村的情況不是個案。受訪基層干部反映,如果不根據搬遷安置點的規劃來調整土地利用規劃,安置點的修建將始終面臨用地可能違法的局面。而一旦不能妥善處理好安置點土地權屬的問題,未來還有可能在搬遷群眾和基層政府中產生新的矛盾。對此,區縣建議在今后的安置點建設過程中,根據安置點規劃,對所涉及的鄉鎮給予調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機會,讓安置點建設手續合法,并能夠及時給搬遷群眾辦理房屋土地權屬證,不讓搬遷群眾搬遷過后喪失對土地占有的合法權利。 無地可供如何解決? 在武陵山區貧困縣酉陽縣黑水鎮大泉村鄉村旅游安置點,當地政府將生態扶貧搬遷安置、鄉村度假旅游及周邊工業園區有機結合,有效解決群眾的安置問題和搬遷后的生計問題,得到老百姓的肯定。黑水鎮副鎮長陳烈陽告訴記者,鎮上本打算將這個安置點進一步擴大,卻遇到了無地可供的難題。 陳烈陽說,黑水鎮幅員面積230平方公里,90%都是山地,能夠讓搬遷群眾滿意的安置點選址肯定得在公路沿線這樣交通方便、地勢平坦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公路兩旁這些稍微平坦的地方已沒有建設用地指標。下一步如果土地不能調規,就沒辦法再擴建。 高山生態扶貧搬遷涉及50萬人,遷入地建設用地無指標或違規建房,成為區縣國土部門反映強烈的問題。他們表示,通過宅基地復墾、增減掛鉤等政策,能有效解決新建安置點的部分用地指標問題,但指標能不能落地,還要看安置點選擇的位置是否符合當地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此外,本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受現行國家相關農村土地政策和各搬遷居民安置點土地資源稟賦的客觀條件制約,要給搬遷戶在“新家”附近全都分配一定面積的口糧(蔬菜)田,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目前看來難度較大。 重慶市扶貧部門介紹,重慶農民人均耕地不足1畝,如果按人均擁有不低于0.5畝基本口糧(蔬菜)田計算,未來5年至少需新調劑50萬畝耕地。搬遷人口與遷入地可供調劑土地的矛盾十分突出。 56歲的酉陽縣桃花源鎮梁家堡村9組貧困戶吳啟貴,對搬遷后能不能分到土地十分看重。他說,在山上雖然交通不便,但自己每年種幾畝地,還能保證全家人的口糧和日常蔬菜。“如果搬下去了沒有田地,自己年齡大工廠又不要,以后全家人吃米吃菜都靠買的話,那生活還是有點惱火了。” 本刊記者發現,搬遷群體中的老年人對土地的依存度仍然較高,而且這一群體不像年輕人那樣容易找到務工機會。因此,搬遷后能否解決口糧田問題,直接影響他們的搬遷意愿。 一些基層干部建議,在規劃安置點的時候要盡量滿足搬遷群眾對土地的基本需求。通過調整、流轉等多種方式,盡可能為搬遷群眾分配一定的口糧(蔬菜)田地。此外,還要為各種年齡階段的搬遷群眾創造更多的務工機會,用工資性收入減弱他們對土地的依賴性。記者劉衛宏 陶冶 李松 趙宇飛 |
- 心情版
- 請選擇您看到這篇新聞時的心情
- 查看心情排行>>